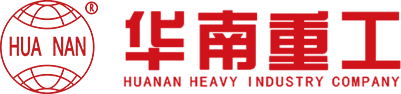多年来,作家夏榆行走世界,前往斯德哥尔摩、奥斯陆,伊斯坦布尔、柏林、华沙、布拉格、东京等地旅行。他以个人体验式写作,重访20世纪风云际会之地,深入阅读对话帕穆克、昆德拉、卡夫卡、苏珊·桑塔格、菲利普·罗斯、J.M.库切、米沃什、克里玛等一代杰出心灵。近期他推出这批随笔的合集《无与伦比的觉醒》一书,聚焦异国城市的人文地理,也对时代剧变中文学大师的思想进行阐发。
“阅读与写作的过程,就是在精神内部构建一个形而上的圣殿。那些真正的杰出者如同暗夜行路时的星辰,有光在我们头顶,脚下的路瞬间被照亮。更多时候,那些贴近心灵的阅读会带给我精神的战栗,歌德说,‘战栗是人性中最好的部分’。”
1995年8月10日,英国诗人斯蒂芬·斯彭德爵士辞世,约瑟夫·布罗茨基追忆故友情义。1972年,布罗茨基被驱逐出境,流亡西方时受到诗人奥登和斯彭德的热忱照护,由此缔结情谊。
布罗茨基曾经追忆自己做过的一个游戏:在伦敦的皇家咖啡馆,到访英国的布罗茨基邀请斯彭德夫妇聚会,餐叙时,以赛亚·伯林与他们同席。他们列出一份“本世纪最伟大的作家”名单: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穆齐尔,福克纳,贝克特。但这份名单只到1950年代为止,八十高龄满头银发的斯彭德问布罗茨基:“如今还有这样的作家吗?”“约翰·库切或许算一个,”布罗茨基回答,“一位南非作家,或许只有他有权在贝克特之后继续写小说。”斯彭德问:“他的名字是?”“我找到一张纸,写上库切的名字,并加上《迈克尔·K的生活与时代》。”布罗茨基在发表于《纽约客》的祭文《悼斯蒂芬·斯彭德》写道。
2003年10月,J.M.库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学院常务秘书霍拉斯·恩达尔(Horace Engdal)宣布这一消息时说:“我们都确信他在文学方面所做贡献的持久价值。我不是指书的数量,而是种类,以及非常高的水准。我认为,作为一名作家,他将继续被人讨论和分析,我们认为应该将他纳入我们的文学遗产。”瑞典文学院在正式报告中说:
库切的小说以结构精致、对话隽永、思辨深邃为特色。然而,他是一个有道德原则的怀疑论者,对当下西方文明中浅薄的道德感和残酷的理性主义给予毫不留情的批判。他以知性的诚实消解了一切自我慰藉的基础,使自己远离俗丽而毫无价值的戏剧化的解悟和忏悔。
我对瑞典学院并不陌生,有三年的时间我在隆冬之季前往那个昼短夜长的北欧之国。一幢位于斯德哥尔摩老城的城堡般的建筑,昔日是证券交易中心,后来成为瑞典学院所在地。走进瑞典学院大楼,踩着石阶,或乘老旧逼仄的电梯,可进入这幢大楼的任何一处。我进入过瑞典学院的会议厅,那里围着一张长桌摆放着十八张宫廷式座椅。拥有18位院士的瑞典学院只有15位参与日常工作,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就由部分院士组成。评委会给库切的颁奖词堪称一个作家所能享有的最高荣耀:
库切的作品是丰富多彩的文学财富。这里没有两部作品采用了相同的创作手法。然而,他以众多作品呈现了一个反复建构的模式:盘旋下降的命运是其人物拯救灵魂之必要途径。他的主人公在遭受打击、沉沦落魄乃至被剥夺了外在尊严之后,总是能够奇迹般地获得重新站起来的力量。
此刻,我想到布罗茨基,他是库切杰出的知己。或许是心存感激,库切在2002年出版的小说《青春》中写到他对布罗茨基的追念。梦想成为诗人的青年库切来到伦敦,过着居无所定的生活。他在忙碌的谋生间隙,唯一的盼头就是回到房间,打开收音机收听BBC第三套节目。在“诗人和诗歌”系列里,库切听到布罗茨基的访谈。当时被控告为“社会寄生虫”的布罗茨基被判在冰封的阿尔汗格尔斯克半岛服五年苦役,其时仍在服刑。在伦敦,库切坐在自己温暖的寓所里,喝着咖啡,咬着有葡萄干和果仁的甜品时,一个和他同龄的人,在整天锯圆木,小心保护着自己长了冻疮的手指,用破布补靴子,靠鱼头和圆白菜汤活着。
“黑得像缝衣针的里面一样。”布罗茨基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他无法从心头驱赶走这行诗,如果他一夜又一夜地专心致志,如果他能够以绝对的专心迫使灵感恩惠降临到他头上,他也许可能想出什么可以与之匹配的句子来。”库切的《青春》叙事,尽显他在漂流的困顿中对诗人的挚爱。
“仅仅在从广播中听到的诗歌的基础上,他了解了布罗茨基,彻彻底底地了解了他。这就是诗歌的力量。诗歌就是真实。但是布罗茨基对于在伦敦的他只能是一无所知。怎样才能告诉这个冻坏了的人,他和他在一起,在他的身边,日复一日,天天如此?”在宇宙之间,两个相距遥远的人,心灵联通,穿越时空。
2021年10月5日午夜,我重新阅读库切的《青春》,在第十一章中找到一个细节,我被这样的叙事震动:
约瑟夫·布罗茨基从颠簸在欧洲黑暗的海洋中的孤阀上将他的诗句释放到了空气之中,诗句随着电波迅速传到了他的房间里。他同时代诗人的诗句,再一次告诉他诗歌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因而他自己可以是什么样子的,使他因为和他们居住在同一个地球上而充满了欢乐。
1970年1月1日,30岁的库切把自己锁在位于纽约州布法罗市帕克大街24号地下室的住所里。他在新年许愿中发誓,如果写不到一千字,就绝不出门。他下决心坚持每天写作,直到完成一部小说的草稿,这就是长篇小说《幽暗之地》的雏形。
库切身上的外套和脚上的棉靴说明房间没有暖气。他用黑色圆珠笔在横格纸上写作,《幽暗之地》的手稿被永久保存在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哈利雷人文研究中心。由《越南计划》和《雅各·库切之讲述》组合而成的《幽暗地带》,是纽约布法罗时期给予库切的馈赠。
2017年10月,我到纽约旅行时带着《J.M.库切传》,仿佛是循着库切的踪迹在美国游走。我知道他曾经在布法罗大学就职,尽管纽约城与纽约州在地理的意义上不是一个概念,仍然觉得距离库切的生活遗迹更近一点。
1970年,库切在布法罗被捕,但并不是因为参加反战示威活动。当时,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校长请数百名警察驻扎在校园,而校长本人则从办公室撤退到一个秘密地方。库切和40多位教师静坐抗议,结果被捕。此次事件是库切职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扼杀了他留在美国的机会,同时开启了他的写作生涯。“在静坐事件之后,我在布法罗教书一直到1971年5月。和45人中的其他人一样被撤回指控,但是因为我的违法案底(尽管后来上诉成功),我的签证在移民和入籍当局看来极为复杂。我的再入境签证被撤销,使我不得再回美国。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在1971年决定辞职,并离开了美国。”
库切由此开始了他第一部长篇小说《幽暗之地》的写作。他将《雅各·库切之讲述》的手稿寄给了总部在纽约的詹姆斯·布朗文学代理公司。从一开始他就明确要将自己的作品投入国际市场,他不想被定义成一位来自殖民地的作家。《雅各·库切之讲述》曾被四家出版社拒绝,后来丰富为《幽暗之地》的原稿也被多家出版社拒绝。
“生活没有安慰,没有尊严,没有仁慈的承诺,我们所面临的唯一的责任——尽管莫名其妙又很徒劳,但仍然是我们的责任——是不要对自己撒谎。”这是库切2007年在文论集《内心生活》中对他的文学榜样塞缪尔·贝克特的阅读鉴识。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职业榜样,库切青年时就开始大量阅读贝克特的作品并深受影响。2007年他在《纽约书评》发表关于作家和书籍的真知灼见,这些文字集结为《内心生活》。
1969年,库切被授予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标题就是《塞缪尔·贝克特英文小说文体研究》。为了能够引述贝克特的《徒劳无益》,他在1968年3月19日写信给查托温达斯出版社。出版社要求库切标明需要引用的部分,否则拒绝许可。库切收到回信后,告知了确切引用的部分,出版社回函允许他将贝克特的部分内容放在论文的附录部分,但有一个附带条件——如果以后库切将博士论文出版,需要再次征询他们的意见。贝克特对版权的保护可以从出版社给库切的信里所引用的贝克特的要求中看出:“允许你引用(最多十次),每次不可以超过十行(以查托温达版为准)。”这让库切第一次体验到一位着名作家是如何严格保护自己的着作权的,并引导库切学会如何保护自己的创作权益。更重要的是,贝克特的美学原则和世界观对库切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一如普鲁斯特、卡夫卡、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的影响,构成了库切的文学精神承继。
库切的自传三部曲《男孩》《青春》《夏日》及其总题“外省生活场景”,令人想到托尔斯泰的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作家罗斯玛丽·埃德蒙兹(Rosemary Edmonds)对托尔斯泰企鹅版三部曲的评述,也是库切的自况:
当他还是一个19岁男孩的时候,托尔斯泰就向自己的笔记本倾诉,他想彻底了解自己,从那时到82岁去世,他一直在观察和描述着自己的灵魂状态……这并不是对知识的好奇,也不是对智慧的渴求。能够让托尔斯泰一生中持续观察并记录的原因是:对死亡与虚无的绝望和恐惧。
1970年代,库切回到了他一直想要断绝关系的南非。早在1962年库切在伦敦开始计算机程序员的工作时,他的祖国通过了阴谋破坏法(the Sabotage Act)。不少被拘留者是库切早年认识的大学同学,许多人被羞辱、折磨和单独关押,有些人则永久离开了南非。库切在《双重视角》中写道:“黑暗的、外人不得进入的禁室本质上是小说幻想的起源。在制造这些卑劣行为、增加神秘的过程中,国家本身在不知不觉中为小说的再现创造了先决条件。”库切的《等待野蛮人》,讲述的就是酷刑室给一个有良知的人带来的冲击。
这部小说写于1977年9月20日,早期版本是在开普敦大学的考试用纸上撰写的。小说先后有三个版本,也是库切辗转生活的写照,开始写作的时候他在开普敦,写作过程中他已到了美国,先是在德克萨斯大学,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讲学。
他要等到数十年辛苦写作之后,才终于像普鲁斯特那样明白他一直都是知道他的真正题材的。而他的题材就是他自己——他自己和他作为一个在一种不属于他(他被告知)和没有历史(他被告知)的文化中成长的殖民地人,想在世间找到一条出路所作的一切努力。既然没有良好的条件,他必须自己在世界上闯出一条路来。
这是南非作家J.C.坎尼米耶在《J.M.库切传》中的评述。消瘦的身材,花白的胡子,低沉的声音,戴着角质眼镜,有着沉默寡言的风范和清心寡欲的外观。多年来,库切用沉默和拒绝来保护自己不受外界入侵,记者的采访是困难的,他的私人生活处于公共领域之外。他离异,和他的两个孩子——尼古拉斯和吉塞拉住在郊区狭窄街道上的房子里。他的伴侣多萝西·德莱弗有自己的住处,而不是总与他住在一起。他是素食主义者,1980年代被诊断患有乳糖酶缺乏症,不能吃任何奶制品。当他罕见地出现在社交场合时,宁愿站在一个角落里跟人说话。
我对库切的阅读有着漫长的时间,最初是《夏日》,讲述他的生活,他的写作,他的情感和欲望,他的挫折和失意。这是一部幽暗荒凉的书,也是进入库切的内部世界、勘查他的精神景观的一个文本。
▲ 效仿T.S.艾略特1944年的文章《何为经典》,库切于1991年在奥地利格拉茨发表了同名演讲
库切的工作是研究世界,然后书写。他的写作是一场探索存在性的浩大工程。库切在中国出版的所有着作——长篇小说及文学评论集,每一部我都很喜欢。如沉痛挽歌的《彼得堡大师》,冰冷的《铁器时代》,对脆弱人性勘察入微的《迈克尔·K的生活与时代》,对邪恶和非正义直抒胸臆的《凶年纪事》,残酷而哀伤的《耻》以及驱除虚火、波澜不惊的《耶稣之子》,这些作品都令我感到库切叙事的精准和出神入化,体会到库切写作独有的冰冷美感和残酷诗意。包括文论集《内心生活》《异乡人的国度》,更可窥见他对写作的理想和信仰。
然而我觉得这些阅读对于理解库切的价值还嫌不够,中文世界的库切依然简化,直到2017年10月读到《J.M.库切传》。这是在更广阔也是更深入的背景下对一个杰出作家的精神考察,也是在更多元更开放的语境下对一个优秀知识分子心灵的呈现。最重要的是我由此看到一个杰出小说家应有的道德维度和人格标高。
上一篇:有关我不能失信到底是个什么梗? 下一篇:关于孙淳有孩子吗有没有后续报道?
- ·江苏卫视人间栏目这是不是真相?
- ·将爱情进行到底剧情介绍网友如何看?
- ·罗湖区城管和综合执法局胡维衡局长组织调
- ·假面公主的滴泪痣是真的吗?
- ·香港急推“0+0”风险大!疫情存变数新变
- ·旗(qí)开(kāi)得(dé)胜(shèng)究竟怎
- ·央行超额平价续作1700亿元MLF利率连续8个
- ·度宇宙什么是度宇宙?度宇宙的最新报道
- ·妄想萌少女到底什么情况?
- ·关于医者仁心观后感网友关心什么?
- ·关于不懂爱情歌词究竟什么情况?
- ·关于欧洲历史剧具体内容!
- ·告五人个人资料乐队名字由来引关注主唱犬
- ·《家在古城》:记录时代浪潮中的古城之变
- ·有关巴神前女友科菲什么原因?
- ·【京研教育】 2020年央财国际商务考研真
- ·清明节放假通知到底是什么情况?
- ·万丈深渊(wàn zhàng shēn yuān)网友
- ·关于东方不败之与尔同生最新消息!
- ·男人大实话之心太软究竟什么原因?
- ·关于惠州不锈钢保温水箱可以这样理解吗?
- ·生均由650元提高到720元!中央财政安排15
- ·关于含羞草的外形特点是真实还是虚假消息
- ·夺叮矮(ǎi)莹(yínɡ)是个什么梗?
- ·惠锋新科(870825):公司对外投资设立控
- ·c照几年一审c照多少年一审
- ·关于德达侦探所官方博客怎么上了热搜?
- ·有关六龄童章宗义会造成什么影响?
- ·顶天立地男子汉这是一条可靠的消息吗?
- ·泰国有多少人口泰国的人口有多少